文质互彰 赏用相悦 ——关于端砚美的欣赏要旨浅论
2019年12月28日 16:30
文质互彰 赏用相悦
——关于端砚美的欣赏要旨浅论
刘演良 卫绍泉
端砚何美?
美在品质,美在石品花纹,美在致用,美在文质彬彬。
端砚之美,美在文质互彰。其石质细腻、娇嫩、滋润、致密坚实,其石品花纹色彩绚丽多姿,形态丰富多彩,文质互彰,一美也。端砚之美,美在赏用相悦。或方圆有度、规矩得法,或随石赋形、肖物得趣,用与赏相悦,二美也。端砚之美,美在天人和合。锦上添花显神功,因材施艺见工巧,天人合一,三美也。端砚之美,美在秀外蕙中。内蕴仁德品格,外饰合仪之礼,秀外而蕙中,四美也。
一、端砚之美,美在文质互彰
端砚自唐代面世开始,就以其石质细腻、娇嫩、滋润、致密坚实的品格傲视群砚,独尊众砚之首。何故,其质之特点与墨亲和的绝配功能使然。前人谓端砚石“细腻如玉”,“温软嫩而不滑”,“贮水不耗、发墨不损毫”,“久用锋芒不退”,“下墨快,发墨佳”,磨之寂寂无纤响,手感如杵搅热釜中的黄胶,油油然墨下如生轻烟;触手而酥,呵气成云;抚之温润幼嫩,犹抚小儿肌肤,令人心摇神荡。就连皇帝宋徽宗也称其为“紫玉”,或可知其堪宝矣。
端砚的自然美,更多地表现在纹理精美、石品花纹绚丽多姿的层面。这些优美的石品花纹与细润如玉的石质结合在一起更臻完美。优美的石品花纹不仅具有视觉上的审美愉悦价值,更有其微妙的实用价值。它们一般以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物态来命名,生动而有趣;其千奇百态的形式,亦藏亦露的形态,令历代文人墨客诗情大发,留下大量精典的美文。
天青——是端砚石中最高贵的石品。其“如秋雨乍晴,蔚蓝无际。”有色深、浅两种,深天青深沉寂穆,浅天青妖娆秀丽。它常与青花共生,“质细而润,色纯而润,沃水则如紫气滃郁,颇移人情”(孙森语)。其色古朴高雅,深沉凝重,颇受文人墨客青睐。天青“生”浮云,如秋日之蓝天伴白云,魅力照人,怡人心性。其质地特别坚润,发墨特佳,名贵古砚多为天青石质。
冻——是端砚石中质地最细腻、最幼嫩、最具观赏性的石品表现形态,呈凝脂状。根据其形态可分为澄潭月漾的鱼脑冻,白如晴云、吹之欲散的浮云冻,如群珠散落、蹦点跳动的米碎冻等。
石眼——是端砚石中最神奇迷人的石品,清潘耒形容石眼:“人惟至灵,乃有双瞳,石亦在眼,巧夺天工,黑晴朗朗,碧晕重重,如珠剖蚌,如日丽空。”前人根据其大小与特征,美其名为鸲鹆眼、鹦哥眼、鸡公眼、象牙眼、绿豆眼等十多种,各有其观赏之妙。
蕉叶白——是端砚石中质地最纯净最微妙的石品。“浑成一片,净嫩如柔肌,如凝脂。”有含露欲滴之感。
青花——是端砚石中最惹人怜爱又捉摸不透的石品。其微小而无质,以多种形态寄生于各种石质石品中,其“妙在隐现中”,以“如细尘掩明镜,墨沈濡低者为绝品”。
冰纹——这是端砚石中最浪漫迷人的石品,唯老坑独有。其状似线非线,如纱似雾,特别是与冻和蕉叶白融在一起,其温润之色可餐,鲜活之色欲滴。
这是端砚中既具观赏性又具实用性的石品花纹,它们常组合地出现在优质的砚石中,其千奇百变的形态,亦隐亦现的形式,特别是石品组合生成美妙神奇的象形图案,更给欣赏者带来丰富的联想空间和回味无穷的余地,慢慢地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审美体系。
端砚石这种质与文互彰的奇特属性,乃大自然恩赐,作为有用之器材,能有此美质美品,世间少有。正是这种神奇的石头,让无数文人士大夫不惜恭身下礼,与其结为知己。正是这种亲和的关系,砚之美质默默地渗透和滋润着文人寂寞的心,砚之美品也不断兴发着文人的诗心,于研磨濡染、摩挲玩赏之中成就功名。
二、端砚之美,美在赏用相悦
前人有所谓“玉不琢,不成器”,端砚石亦然,只有将质优品美的端砚石制成适用于研墨的器具,端砚石的美,才能得以被人赏识,也才真真正正地产生它存在的价值。
端砚石从唐代开始被发现为制研之良材,即引起了文人士大夫之关注与重视。“知者”、“巧者”共同努力,在前朝风字砚的基础上创造出砚台新的典范——箕形砚,这种砚台轻便而不失庄重,简洁而又充满张力,实用而又雅致,显示了大唐盛世的时代风尚。宋代延续这种审美取向,改良箕形砚为抄手砚,从形式上融入宋理学的价值观,其外形朴素大方,堂堂正正,实用雅观,成为砚史上又一典范之作。近代学者大都评论唐箕宋抄手制作简单,只重实用,我们认为:唐箕宋抄手之所以被认为砚台史上的两座高峰,是因为从造物的角度来说,其形式与功能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从文化层面上说,其简、其素正体现了儒家君子理想的道德境界,一方面他们认为好砚石“质有余者,不受饰也”。(孔子语)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无雕饰为最高级的装饰。实际上唐箕宋抄手并非无雕饰,而是以看不见的饰(抽象的造型与形式)为饰,以质(砚石的美质)为主饰。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与审美取向也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砚台造型和形式的变化,但无论如何,重实用、重石质以及重石品花纹的审美取向一直没变,直至今天依然如是。制砚人始终都会把端砚石中石质最好,石品最丰富、最优美的部分安排在砚堂中,而且尽可能地让砚堂占据主要的面积,以保证研磨墨条舒展畅快的感觉和研墨的效率和质量,故而,墨堂至少要占整个砚面的三分之二以上,才能保证研墨过程的舒适感和愉悦感得到满足,也才能让欣赏者有足够的空间欣赏到端砚的天然美质美品,就算砚堂未能囊括全部优异的石品,制砚人也不会随便雕刻,而且会想办法将其保留或修饰美化,让欣赏者获得更多美的感受与遐想。因而,我们认为,砚堂是砚台的灵魂,也是砚之为砚的最为独特的个性,欣赏一方砚台,只要观看砚堂,就基本可以为其作出合理的价值评价。就砚而言,今天我们也许很少用砚台(特别是名贵的砚台)研墨,但如果一方砚台不能用,或不能很舒适地使用,那它绝不是一方好砚台。我们不用,是因为它太名贵了,舍不得用,或者是它的石品花纹太美了,我们舍不得沾污它。
三、端砚之美,美在天人和合
让端砚美石成为适合研磨之器具,这是制砚的本源。但是由于端砚石本身的石性特质以及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对砚台的审美情趣的需求不同,使砚的工艺在保证实用功能之外增加了纹饰和图案的美化装饰。
端砚石是天然石材,是含铁泥质页岩或含粉沙的泥质板岩与水云母、绢云母、石英和多种铁矿等多种矿物,经几亿年的化学、物理作用和地质变动而成。其石生长结构独特,能符合制砚标准的优质砚台(石肉)只有25cm-60cm左右,固开采出来的砚石原料大部分是瑜瑕并存,“石材之大者尤为难得,每求购方六、七寸而无病脉者,固亦小矣。”(清?吴兰修《端溪砚史》),特别是三大名坑中的老坑和麻子坑。因而在端砚的制作中“因材施艺”成为最基本的技艺。这不仅要求制砚艺人要有入石三分之眼力,而且要熟悉砚石的变化规律和制砚工艺的规与范,惜材而尽材之用。我们认为,端砚的制作不是为雕刻而雕刻,而是有目的的艺术加工。一是尽砚材的可能,最大可能地满足研墨的功用。无瑕之材,我们不忍心动刀,应由形式和天然纹饰去雕饰,无须“为赋新词强说愁” 。比如一方石质纯净无瑕的素砚、平板砚,就是最高级的雕刻,其温润如玉的石质和充满美感的石品,就是对砚台的最好装饰了。二是在满足实用的前提下,或以恰当的雕刻手法彰显石质石品之美,以体现制砚人的巧思,或雕刻图案、图象以表达、寄托自己的情趣,或作简单的装饰美化砚台,让使用者在研墨、观赏之时,有手感、有观感、有情趣、也有遐想等丰富性体验。三是变有瑕为无瑕,以多种雕刻手法,去掩盖砚石中的瑕疵,甚至达到化瑕为美的艺术情趣。这要求制砚师匠在审美的造型、书法绘画、雕刻技法以及传统文化艺术方面有一定的修养和造诣,才能达到锦上添花的艺术效果。
近年来,在制砚的圈子里,出现了一些令人忧心的现象,片面强调砚材之大,甚至取不能为砚之砚材强之为砚,以铺满砚石的雕刻掩盖材质之劣;片面强调手艺高超,妄视砚的材质和多姿多彩的石品花纹,以繁复、锁碎工艺彰显个人的“能力”。一些媒体不明事里,受其误导,并为其大肆吹嘘,成为“助纣为虐”的吹鼓手。我们认为,优质的砚材当然是越大越好,但这只是凤毛麟角,而大而无当则有不如无。砚雕不是石雕,也不是牙雕、木雕和角雕等架上工艺品以追求精雕细刻中见价值和工巧的高低,砚台是具有欣赏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文房四宝之一,而不是纯粹作为欣赏、摆设的工艺品。砚台的创(制)作有其自身独特的规范和审美取向,端砚价值的高与低,不在于雕刻的多与少,在乎石质是否适合研墨,在乎石品花纹是否美不胜收,在乎使用过程中的舒适度和愉悦感,在乎工艺构思的巧妙,在乎由砚生发的文化附加值,在“用”与“赏”是否统一,综合而言,砚台的最高境界在于“天工人工、两臻其美”。
四、端砚之美,美在秀外慧中
端砚能成为文房四宝之一,四大名砚之首,能成为帝王将相、文人士大夫宠爱有加的对象,并以其朴质沉厚之德,兼有奇相体貌,获封“即墨侯”之尊称(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可以说皆因其石质之优与石品花纹之美的完美结合所生成的研磨功能和其所申发的人文意趣。就质而言,其温润而粟的质性,磨而不磷的品格,端方厚重的品貌,坦荡包容的气质,恰好与儒家倡道的君子品德--温厚刚直,体备用周的德性才识相合。就其石品花纹而言,正应文人士大夫感物起兴的诗性情怀和“素以为绚”的审美取向。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端砚质负玉德,身载材器,品赋情趣,纹蕴诗意的器量,秀外蕙中、文质彬彬的德性,才会改变历代文人士大夫数千年俯看砚台常态,开始平视砚台,与砚台称兄道弟,与砚为犮、终身相伴、亲切交流,更有甚者时时仰望其尊贵的姿容,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有诗文为证:“……嘉其谨默,诏命常侍御案之右,以备濡染,因累勋绩,封之即墨侯”(唐·文嵩,见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四之辞赋》)。“润比德,式以云。绕玉池,注天潢。永年宝之,斯为良。”(褚遂良《题端溪石渠砚》)。“端州石砚人间重,赠我因知正草玄”(刘禹锡《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鉴之》)。“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文天祥·岳飞砚铭)……无数赞美端砚的诗文以及发生在端砚中的姻缘际遇故事蔚为大观,并在不断的申发中。
正是端砚具有的质润纹美的天赐特质,并能与实用结合得圆融无碍,才能使其得以超越砚台于器物层面的工具性而上升到形面上的层面,并恰好与儒家所谓的“文质彬彬”的理想和标准相吻合,也恰好发生在与使用者的文人士大夫朝夕相濡的亲密接触。这是端砚之幸,也是文人之幸也。
以“文质彬彬”的理念具体落实到砚台上,一方面体现在材质和石品花纹与雕刻的关系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实用功能与砚台的造型和形式的关系上,再则是体现在砚台的物理方面的性能与社会人文道德的关系上。端砚中的质,不仅是对自然材料的运用,对研墨功能的追求,也是对外在造型、形式的美感追求; 在一定的层面上,也体现着制砚人、赏砚人的一种时代审美价值观和伦理观。端砚中“文”也隐含着对功能的本质要求,也是文化、艺术价值观的体现。无论端砚在何种层面上的关系,最终都指向“质”与“文”的和谐。
以上我们从四个层面论述端砚之美,美在石质、美在石品花纹,美在实用,而更重要的则是美在“文质彬彬”。这四个层面各有自己独立的审美情趣,也互相交融,不断生发出新的审美意象。这些具有独特个性的审美意象,不断丰富端砚之美,也不断淀积砚文化体系的深厚内涵。如果端砚的发展能将各种层面的功用最终指向并落实在内的“质”,那么其“质”本身已达到至美,而无须任何纹饰了。我们认为,端砚的欣赏,恰如人们自我观照自身,如果人们经过长期的修身养德,使内心情感莫不合乎于礼仪之文,也就是说“质”己达乎“文” 之赏, “质”本身就是“文”,又何须外在地强之为“文”呢?一方砚石如果经过能工巧匠的智慧和灵动的双手,使之达到了“质”亦“文”,“文”亦“质”的境界,亦即达到了“用”与“赏”圆融,那就是对端砚美最好的诠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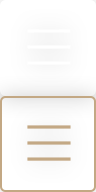

 粤公网安备 44120202000322号
粤公网安备 44120202000322号